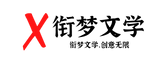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江湖人最爱吟诵的,便是这李白的《侠客行》。
诗中侠客的豪迈不羁、重诺轻生,恰是这片以武为尊的天地里,无数人心中的图腾。
只是千年以降,真正能称得上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的侠客,早已成了传说。
更多的,是为了爵位、为了秘籍、为了那虚无缥缈的 “至尊皇者” 之位,在刀光剑影里厮杀不休的芸芸众生。
华夏大地,九州鼎立,烽烟从未真正停歇。
自夏朝初年,姒启令太史司马氏订立武学爵位制度以来,江湖便被这森严的等级牢牢捆缚 —— 五等男爵、四等子爵、三等伯爵、二等侯爵、一等公爵、盖世帝者、至尊皇者。
每一阶的晋升,都意味着力量的暴涨,以及随之而来的权势与敬畏。
传闻中,男爵便可开碑裂石,子爵能纵跃数丈,伯爵可气劲外放,侯爵已能御风而行,公爵则是移山填海之能。
至于那盖世帝者,五方之地各有其一,皆是活了数百年的老怪物,轻易不踏足凡俗。
而至尊皇者,自制度订立以来,四千余年,竟无一人能登顶,只留下一个空悬的宝座,引得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制度,如同悬在江湖头顶的日月,夏灭商替,商亡周续,王朝更迭如走马灯,唯此等级岿然不动。
到了如今的大宋,已是赵氏皇族执掌社稷近两百年,可这江湖的规矩,依旧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铁律。
时值宋徽宗重和二年,这天下早已是风雨欲来。
北方大旱,赤地千里,辽国与西夏趁机联兵南侵,边关烽火连天,尸骨成山。
南方虽无兵戈,却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百姓易子而食者,早已不是新鲜事。
庙堂之上,徽宗沉迷书画奇石,自号 “道君皇帝”,终日与蔡京、童贯等奸佞为伍,将相离心,宗室间为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从未停歇。
江湖之野,更是乱成了一锅粥。
近千年来未有至尊皇者出世,使得各大门派、世家大族对 “盖世帝者” 之位觊觎不已,明争暗斗,血雨腥风几乎成了常态。
荆楚之地,大宋南疆,毗邻大理,恰是三不管的蛮荒之所。
这里群山连绵,瘴气弥漫,既非朝廷重点管辖之地,也非名门大派的根基所在,成了流民、盗匪、以及一些躲避仇家的江湖客的容身之处。
滁州城,便是这片蛮荒之地边缘的一座小城。
说是城,其实规模只比寻常镇子大些,城墙是用当地青石砌成,历经风雨侵蚀,早已斑驳不堪,多处墙皮剥落,露出里面暗黄色的泥土。
城门口没有官兵守卫,只有两个歪歪扭扭的石狮子,一只缺了耳朵,一只断了前爪,透着一股破败之气。
这日黄昏,夕阳如血,将半边天空染得通红。
城外的青石大道上,尘土飞扬,归乡的乡民们络绎不绝。
他们大多是附近村落的农人,或是去城里做些小买卖的商贩,此刻都脚步匆匆,脸上带着疲惫,却又有着一丝对家的期盼。
挑担的汉子肩上压着沉甸甸的柴草,扁担在肩头咯吱作响,他时不时用袖子擦一把额头的汗,粗重的喘息声在寂静的黄昏里格外清晰。
提篮的妇人小心翼翼地护着篮子里仅剩的几尺布料,那是她用攒了半个月的鸡蛋换来的,要给家里娃做件新衣裳。
背筐的老妪佝偻着腰,筐里装着些野菜,这是今晚的口粮。
城门口右侧,靠着城墙根,搭着一个简陋的草棚,棚下支着一个乌黑的大炉子,炉子里的炭火早已熄灭,只剩下些许余温。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正慢悠悠地收拾着摊位,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袖口磨破了边,露出黝黑干瘦的手腕。
老汉脸上布满了皱纹,如同老树皮一般,眼角的皱纹尤其深,几乎要将那双眼睛完全遮住。
他动作迟缓,将一片片没卖完的烧饼仔细地码进竹筐里。
那些烧饼是用粗面做的,个头不大,表面有些焦黑,却散发着一股朴素的麦香。
老汉的动作很轻,仿佛那些不是烧饼,而是什么稀世珍宝。
他身前的油锅还在微微沸腾,残留的油星子时不时溅起,在夕阳下闪着微弱的光。
离草棚不远,城墙根下有一条臭水沟,沟里积着墨绿色的污水,散发着刺鼻的腥臭味。
沟边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枯黄的草叶在晚风中摇曳。
草丛深处,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老汉那双拿烧饼的手。
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啊?
黑白分明,亮得惊人,像是藏着两颗星星,可此刻,这双眼睛里却只映着那竹筐里金黄的烧饼,以及难以掩饰的渴望。
眼睛的主人,是个约莫十岁左右的小叫花子。
他浑身脏兮兮的,头发像一蓬乱糟糟的茅草,纠结在一起,沾满了泥土和草屑。
身上裹着一件破烂不堪的棉袄,看样式是去年冬天的,如今早已失去了保暖的作用,棉花从破洞里露出来,黑乎乎的。
他的脸被污泥糊着,看不清模样,只能看到一个尖尖的下巴,和因为极度饥饿而微微凹陷的脸颊。
这小叫花子已经两天没正经吃东西了。
昨天清晨,他在一个大户人家的垃圾堆里翻到了半块被扔掉的黑馒头,那馒头又干又硬,还带着霉味,可他还是像珍宝一样,小口小口地啃了一整天,到现在,肚子里早已空空如也,饿得他头晕眼花,四肢发软,只能无力地靠在冰冷的城墙根上,喉咙不停地上下滚动着,吞咽着口水。
“要是能有一口烧饼吃,死也值了。” 小叫花子在心里默默地想。
他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爹娘是谁。
记事起,他就跟着一个捡他回来的老叫花子在这滁州城附近讨生活。
老叫花子去年冬天染了风寒,没挺过去,就剩他一个人了。
老叫花子活着的时候,经常给他讲江湖故事,说那些大侠如何飞檐走壁,如何一剑断山,如何一诺千金。
小叫花子听得入迷,常常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那样的人,不用再挨饿受冻,不用再被人欺负。
可幻想终究是幻想,现实是,他现在连一口热乎的烧饼都吃不上。
就在小叫花子的意识快要被饥饿吞噬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突然从西南方向传来。
“哒哒哒…… 哒哒哒……”
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响,像是密集的鼓点,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地面似乎都在随着马蹄声微微震动,大道两旁的野草被马蹄扬起的风吹得倒向一边。
城门口的乡民们顿时停下了脚步,脸上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
“这是咋了?这么多马蹄声?” 一个挑柴的汉子放下担子,眯着眼睛望向西南方向。
“看这架势,怕是有不少人。” 旁边一个提着篮子的妇人紧紧攥着篮子,声音有些发颤,“不会是官兵来抓壮丁吧?前几天听说北边打仗,朝廷抓了好多人去充军呢。”
“不像官兵。” 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捋着胡须,眉头紧锁,“官兵行军有章法,哪会这么乱糟糟的?我看呐,怕是山里的盗匪。”
“盗匪?” 妇人大惊失色,脸色瞬间变得惨白,“那可怎么办?我们快跑吧!”
她的话音刚落,马蹄声中就夹杂着一声声呼啸,那些呼啸声尖锐刺耳,带着一股蛮横的戾气,让人不寒而栗。
紧接着,四面八方都响起了同样的呼啸声,此起彼伏,像是一张无形的大网,正缓缓收紧,将滁州城的城门团团围住。
“快跑啊!山贼来攻城啦!” 不知是谁发出一声凄厉的尖叫,如同点燃了引线,城门口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乡民们惊慌失措,四处奔逃,哭喊声、惨叫声、孩童的啼哭声混杂在一起,场面混乱不堪。
挑柴的汉子顾不上柴草,拉起身边的孩子就往城里跑;提篮的妇人被人群推搡着,篮子掉在地上,布料散落一地,她也顾不上去捡,只顾着埋头往前冲;背筐的老妪跑得慢,被后面的人撞倒在地,筐里的野菜撒了一地,她挣扎着想爬起来,却又被人踩了一脚,只能无助地哭喊。
小叫花子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他下意识地往身后的草丛里缩了缩。
半人高的野草正好将他瘦小的身子完全遮住,只留下一双眼睛,惊恐地望着外面混乱的景象。
就在这时,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声猛然响起,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压倒了所有的嘈杂声。
“吼 ——!”
那吼声雄浑无比,带着一股沛然莫御的气势,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头晕目眩。
正在奔逃的乡民们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般,一个个呆立在原地,动弹不得,脸上写满了恐惧。
连那些刚才还在呼啸的马蹄声,也在这声怒吼后,诡异地停顿了下来。
小叫花子更是吓得浑身发抖,死死地捂住嘴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
“乡亲们!”
一个粗狂的声音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随着这声音,西南方向的那群人马已经清晰可见。
为首的是一个虎背熊腰的壮汉,身高足有八尺,膀大腰圆,站在马背上,像一座小山。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短打,裸露的胳膊上肌肉虬结,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
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背后交叉插着两柄门板大小的巨斧,斧刃寒光闪闪,一看就锋利无比。
这壮汉脸上横肉丛生,一道狰狞的刀疤从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让他本就凶狠的面容更添了几分戾气。
而在他的眉心处,赫然印着七颗黑色的星辰,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在夕阳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诡异。
“大伙都站在原地别动,” 壮汉大声喝道,声音如同洪钟,“刀剑无眼,被划伤了就不好了。”
他话音刚落,突然从身后抽出一柄巨斧,手臂猛地一挥。
只听 “呼” 的一声,一股狂风凭空卷起,他身前不远处一块半人高的巨石,竟被这股风扫得四分五裂,碎石飞溅,火星四射。
乡民们吓得魂飞魄散,不少人腿一软,直接瘫倒在地。
壮汉见状,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狞笑,又催马前进了几步。
就在这时,西边又窜出来一伙人。
这伙人约莫有二十来个,个个骑着高头大马,头戴斗笠,帽檐压得极低,遮住了大半张脸,只能看到他们紧抿的嘴唇和线条紧绷的下颌。
“大伙都不要动哦,” 一个阴测测的声音从斗笠下传来,带着一丝戏谑,“想吃‘油条’的,就动吧。”
说话间,这伙人齐刷刷地扬起手臂。
只见他们手中握着的,竟是一柄柄手腕粗细、通体乌黑的青铜大锏。
锏身打磨得极为光滑,在夕阳最后的余晖下,闪耀着冰冷的光泽,一看就分量十足。
“油条”,是江湖上对被铜锏打断骨头的人的戏称。
这伙人一出手,就透着一股狠戾之气。
乡民们哪里还敢动弹?一个个浑身像筛糠一样瑟瑟发抖,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
刚才还哭闹不止的婴儿,也被父母死死捂住嘴巴,只能发出呜呜的闷响。
一时之间,滁州城门口静得落针可闻,连风声都仿佛停止了。
只有那些战马时不时打个响鼻,甩甩尾巴,提醒着人们这里并非绝境。
草丛里的小叫花子屏住了呼吸,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 “咚咚” 的心跳声。
过了好一会儿,见外面没了动静,他以为那些人都走了,便小心翼翼地从杂草丛中探出一颗乱糟糟的小头,睁着大眼睛,好奇又恐惧地看着不远处的场景。
就在这时,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响起。
“嗒、嗒、嗒……”
那是钢靴踩在青石板上的声音,每一步都落得极慢,却又极重,仿佛每一脚都踩在了众人的心尖上,让人心头发紧。
脚步声越来越近,夕阳将那人的身影拉得老长,投在地上,如同一个巨大的鬼魅。
城门口的众人都惊呆了,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那个身影,连呼吸都忘了。
只有那个卖烧饼的老汉,依旧在慢条斯理地收拾着自己的摊位,仿佛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即使那钢靴声已经近在咫尺,他也没有抬头看一眼。
“嘿嘿。” 那人冷笑了一声,声音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
紧接着,一只盆钵大的巴掌,“啪” 地一声搭在了老汉的推车上。
卖烧饼的老汉这才缓缓抬起头,看向近前的人。
只见这人同样生得五大三粗,满脸横肉,眉心处也印着七颗黑色的星辰,与刚才那个壮汉如出一辙。
“大爷,买饼吗?” 老汉的声音沙哑而平静,听不出丝毫波澜,“两文钱三个,还是热乎的。”
说话间,他低头从竹筐里拿起一个还带着余温的烧饼,递到了来人身前。
草丛里,那双亮晶晶的眼睛瞬间就被老汉手中的烧饼吸引了。
那烧饼金黄油亮,表面还沾着些许芝麻,在夕阳下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满口生津。
小叫花子的喉咙又开始不停地蠕动起来,肚子也不合时宜地 “咕咕” 叫了起来。
他赶紧捂住肚子,生怕被人发现。
“哼!” 那满面横肉的壮汉猛地一把夺过烧饼,劈脸就向老汉砸去,怒骂道:“姓赵的,都到这份上了,你还敢调侃大爷!”
卖饼老汉头微微一侧,动作看似缓慢,却恰好避开了飞来的烧饼。
只听 “啪” 地一声,烧饼重重地落在了城墙外的那条臭水沟中,溅起一片污浊的水花。
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也随着烧饼划了一个弧线,最后死死地盯在了那落入水中的烧饼上。
虽然沾了污水,但那金黄的颜色依旧显眼。
小叫花子眼巴巴地看着那离自己只有一丈远的烧饼,狠狠地咽了一口口水。
他太饿了,饿到连掉进臭水沟里的食物都觉得是美味。
他那只黑乎乎的小手,不由自主地缓缓伸了出去,想要去够那个烧饼。
“哗啦 ——!”
一声刺耳的木头断裂声猛地响起,将小叫花子吓了一跳,连忙缩回了手,瘦弱的身躯缩得更紧了,紧闭着眼睛,瑟瑟发抖。
“哼,东西交出来!” 那个满脸横肉的壮汉咆哮了一声,铜铃般的大眼中似乎有火焰喷出。他腰间的两柄大斧霍地被握在了手中,斧刃映着最后一丝残阳,闪烁着森冷的寒光。
“识相点,” 壮汉声音突然一沉,将一柄大斧放平,递到老汉身前,斧刃离老汉的脖子只有寸许,“不然,这斧头可不长眼睛。”
“是。” 那老汉弯下佝偻的腰,从箩筐里又拿出一块烧饼,轻轻地放在了壮汉冰冷的板斧上。
“姓赵的,你找死!” 那壮汉见老汉依旧装疯卖傻,顿时怒不可遏,板斧猛地一横,带着呼啸的风声,狠狠地向老汉迎面劈来,“我们早就调查清楚了!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
卖烧饼的老汉看似弱不禁风,却被那板斧扫起的大风吹得如同一张白纸般,轻飘飘地向后飘去,恰好避开了这致命一击。
他慢条斯理地开口道:“怎么星宿庄的人都这般有眼无珠?既然查清了老汉的身份,还敢这么无礼,未免太过大胆了吧。”
说话间,老汉那佝偻着的腰缓缓直立起来。
随着他身体的挺直,一股无形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出来,原本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道精光,整个人仿佛变了一个人,再无半分老态龙钟之相,反而透着一股渊渟岳峙的沉稳。
那壮汉怒斥道:“胆大胆小,大爷这就让你知道!”
话音未落,他手中的双斧猛地一错,一招 “力劈华山”,带着千钧之力,再次劈向老汉头顶。
这一斧势大力沉,空气都被撕裂,发出尖锐的呼啸声。
赵姓老汉身形一晃,如同鬼魅般向左侧飘出数尺,轻松避过。
壮汉的双斧劈了个空,斧刃重重地落在地上,“铛” 的一声巨响,坚硬的青石板竟被劈出两道深深的裂痕。
壮汉见状,丝毫不停歇,粗壮的手腕猛地一抖,浑身肌肉贲张,双斧顺势回收,随即变劈为扫,带着一股狂猛的劲风,向老汉拦腰劈来。
这一招又快又狠,封死了老汉所有闪避的路线。
赵老汉眼中闪过一道寒光,身形猛地一矮,如同狸猫般贴地滑行。
同时,他左脚一勾,精准地踢在那箩筐的底部。
“哗啦!” 一箩筐的烧饼瞬间被踢飞起来,在空中散开,如同漫天飞舞的金色蝴蝶。
随即,老汉身形连动,双手在胸前划过一道道玄妙的轨迹,手影弥漫了整个空间。
那些在空中飞舞的烧饼,仿佛被无形的力量操控着,如同出膛的黄金镖一般,带着簌簌的风声,密密麻麻地洒向那壮汉。
“来得好!” 壮汉大喝一声,双手的板斧舞得如同飞轮一般,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防御圈。
“砰砰砰……” 一片片烧饼撞在斧刃上,瞬间被劈得粉碎,碎屑四溅,如同漫天花雨。
混乱中,一块烧饼被斧风扫到,恰好落在了那小叫花子身前不足一尺处。
可此时,小叫花子却没有去看那块烧饼,他睁大了眼睛,眼中露出了一丝异样的光芒。
刚才那壮汉挥斧的招式,那老汉闪避的身法,在他脑海中如同烙印一般,挥之不去。
他虽然不懂武功,却隐隐觉得那些动作中蕴含着一种奇特的韵律,仿佛天生就该那样。
一时间,他竟忘记了饥饿,忘记了恐惧,只是呆呆地看着。
看着看着,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跟着比划起来。
他学着壮汉的样子,握紧拳头,猛地向前劈出,又学着老汉的样子,脚步轻点,向旁边躲闪。
只是他毕竟年幼体弱,动作笨拙可笑,完全没有领悟到其中的精髓。
可还没等他比划几下,只听得四面八方隐隐传来一阵更加急促的马蹄声,远处的地平线上,已经可以看到漫天的尘土弥漫起来,显然又有大队人马正在靠近。
壮汉闻声,不禁仰头大笑起来,笑声粗狂,震得人耳膜发疼,他浑身的肥肉都在不住地颤动:“哈哈,姓赵的,看来老天都要收你!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那赵姓老汉也听到了马蹄声,脸色微微一变,随即又恢复了平静,只是嘴角不易察觉地抽动了一下:“没想到我区区一个卖烧饼的老汉,竟能引来星宿庄这么多高手围攻,真是荣幸啊。”
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从四周马蹄声传来的方向,有几股不弱于自己的气息正在快速逼近。
显然,对方是有备而来,今天这场硬仗,怕是躲不过去了。
“哈哈,知道就好!” 壮汉狂笑不止,手中的板斧霍地向两边划开,一招 “野马分鬃”,斧影重重,将老汉完全包围在刀锋之中,“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那赵老汉却丝毫不惧,冷哼一声:“小子安敢如此目中无人!”
话音刚落,他那双看似骨瘦嶙峋的手缓缓从油乎乎的长袖中伸出。
随着他手掌的伸出,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变得粘稠起来,隐隐有噼啪的声响传出,那是内力运转到极致,压迫空气产生的动静。
只见老汉的手掌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了血红色,如同浸透了鲜血一般,散发着灼热的气息,威势逼人。
“尝尝老汉这招,追血手!” 赵老汉厉声呵斥,血红色的双手陡然拍出,速度快如闪电,带着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那壮汉脸色骤变,心中一凛,说话都有些颤抖了:“追… 追血手!没… 没想到你居然将追血手修炼到了第六层!”
追血手,乃是江湖中一门极为阴毒霸道的掌法,共分七层,修炼到第六层,掌力可穿透金石,中者血液逆流,爆体而亡,极为恐怖。
这壮汉虽然狂妄,却也知道这门掌法的厉害。
“哼!” 赵老汉冷哼一声,并不答话,掌势依旧迅猛如雷。
那壮汉的脸上还带着惊疑不定的神情,胸口就赫然多了一道血红色的手印。
“噗 ——”
壮汉猛地喷出一口热血,鲜血在空中划过一道凄厉的弧线。
在小叫花子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那个如同小山般魁梧的身躯,竟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倒飞出去,“砰” 的一声重重地砸在地上。
坚硬的青石板在这巨大的冲击力下,顿时布满了蛛网般的裂纹。
“啊!死人啦!死人啦!”
城门口的乡民们再也无法保持镇定,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尖叫,之前被吓得动弹不得的人们,此刻也顾不上害怕了,如同丧家之犬般四散奔逃,连先前那些趾高气昂的骑士,见首领被杀,也吓得魂飞魄散,调转马头就跑,瞬间作鸟兽散。
不远处,马蹄声越来越近,赵姓老汉已经隐约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呼喊声,显然是星宿庄的大部队到了。
他心中一急,目光急速地扫视了一圈散落一地的烧饼,眉头紧锁。
他知道,自己今天怕是难以全身而退了。
有些东西,绝不能落入星宿庄手中。
就在这时,他的眼睛突然一瞥,看到了草丛里那个缩成一团的小叫花子。
小叫花子只觉得浑身一寒,仿佛被一头凶猛的野兽盯上了一般,一股强烈的危机感涌上心头。
他下意识地抬起头,正好迎上了赵姓老汉那双诡谲的眼睛,吓得他浑身瑟瑟发抖,连忙将头往草丛深处埋去,恨不得钻进地里。
耳边的马蹄声越来越近,已经能听到清晰的呼喝声。
赵老汉一咬牙,眼中闪过一丝决绝。
他迅速从怀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好的烧饼,运力于指,屈指一弹。
“嗖!”
烧饼带着破空之声,精准地砸在了小叫花子身上。
小叫花子只觉得胸口一闷,像是被一块石头砸中,眼前一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完了,我要死了。”
他身子一软,一头栽倒在草丛中,彻底失去了意识。
那块让他梦寐以求的烧饼,就落在他身边,散发着诱人的香气,可他已经不知道了。
夜色渐深,天空中的乌云散去,一轮朗月高悬,洒下一片清冷的乳白色光辉。
四野之下,在月光的映照下显得影影绰绰,远处的山峦如同蛰伏的巨兽,只听到荒野的风声不知疲倦地吹来,卷起地上的落叶,发出 “沙沙” 的声响。
“哎呦喂……”
不知过了多久,小叫花子才幽幽地醒了过来。
他只觉得额头一阵剧痛,伸手一摸,摸到一个鼓鼓囊囊的大包,忍不住痛呼出声。
原来他刚才一头栽倒时,正好撞在了一块石头上。
“臭石头,哼!” 小叫花子气鼓鼓地嘟囔着,伸出黑乎乎的小手,四处摸索着,想找到那块让他受苦的石头,狠狠地丢到臭水沟里去。
可他的双手却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显然是饿太久了。
突然,他睁圆了眼睛,耳边传来的风声如同鬼魅的低语,让他心里发毛。
“难… 难道我… 死了吗?”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他顿时慌了神,猛地一窜,从地上坐了起来,双手像是突然有了力气一般,在自己脸上使劲地拍了几下。
“嘶 —— 好痛啊!” 他疼得倒吸一口凉气,脸上传来火辣辣的痛感。
随即,他又立马开心地大笑起来:“哈哈哈,我没死,我没死!”
说着,他如释重负般仰面朝天地躺在了草地上,双手随意地放在草皮上,感受着青草的柔软。
“咦,这是什么?” 他的手突然碰到了一个软乎乎、圆乎乎的东西。
借着皎洁的月光,他把那东西拿近眼前一看,顿时眼睛都直了。
“烧饼!” 他失声叫道,声音里充满了惊喜。
他紧紧地攥着烧饼,心里美滋滋的:“这就是老头说的什么‘不死’什么‘福’来着吧?”
他口中的 “老头”,就是那个捡他回来的老叫花子。
他们俩相依为命了十年多,老叫花子虽然邋遢,却对他极好。
老叫花子总是神神秘秘的,时不时会配置一些颜色古怪的 “灵丹妙药” 给他吃,还会烧一些散发着奇怪味道的药水给他洗澡。
最让小叫花子着迷的,是老叫花子肚子里似乎装着说不完的故事。
每当晚上有空的时候,老叫花子就会搂着他,给他讲天南海北的奇闻异事,讲那些江湖侠客的传奇经历。
“哎呀,要是老头在就好了,有烧饼吃,还有故事听。” 小叫花子突然觉得有些美中不足,手里攥着烧饼,心里却空落落的。
“要不,找到老头,和他一起吃吧。” 他心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咕叽… 呼噜…” 可他的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像是在抗议。
他把烧饼凑到鼻子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一股浓郁的麦香混合着芝麻的香味扑鼻而来,让他顿时口水直流。
“我小小地吃一口,然后再和老头一起分享吧。” 他在心里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手中的烧饼不自觉地就凑到了嘴边。
“呜,真香!” 他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小口,细细地咀嚼着。
烧饼上虽然沾了些夜露,变得有些软乎乎的,但依旧带着一股酥脆的口感,比他以前吃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美味。
“哎呀,真好。” 他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手中的烧饼凑到嘴边,一边小口地啃着,一边抬头仰望着天空。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像是无数双眼睛在看着他,又像是在对他眨眼睛,仿佛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黑色的夜幕下,一群黑影悄无声息地飞过。
小叫花子眼尖,看出那是一对大鸟带着一群小鸟,正往巢穴飞去。
“我有爹娘吗?” 这个念头毫无征兆地冒了出来,让他啃烧饼的动作猛地一顿。
他的心里没由来地一阵翻涌,眼眶也变得热乎乎的,有什么东西想要从里面掉出来。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
记忆深处,似乎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片段,像是破碎的镜子,闪烁着模糊的光影,有温暖的怀抱,有温柔的歌声,还有刺眼的火光和凄厉的哭喊……可他怎么也无法将这些片段拼凑成完整的画面。
“嘎嘣!”
一声清脆的响声从他嘴里传出。
“哎呀,好痛啊!” 小叫花子突然轻呼一声,他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烧饼已经吃了一半,而他刚才一口咬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硌得牙齿生疼。
他小心翼翼地将口中的东西吐到手心,借着月光一看,发现那是一块黑乎乎的铁片,约莫指甲盖大小,形状不规则,边缘有些锋利。
“这卖烧饼的老头真不是什么好人,居然在烧饼里面藏东西。” 小叫花子有些不满地嘀咕着。
他看了看那块铁片,也不知道是什么用处,想了想,随手把它塞进了自己破烂棉袄的口袋里。
再看手中的烧饼,已经只剩下小半块了。
“不吃了,留着和老头一起吃吧。” 他嘟囔着,将那小半块烧饼也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口袋里,然后伸出舌头,舔了舔嘴角剩下的残渣,摸了摸肚子,感觉已经有了七八分饱,身上也有了些力气。
风依旧呼呼地吹着,四野一片漆黑,只有月光洒下的一片朦胧。
远处隐隐传来几声狼嚎,凄厉而悠长,让人不寒而栗。
好在平时老叫花子晚上常常不回来,小叫花子早就习惯了独自面对黑夜,甚至觉得这样的黑夜能让他心里感到一丝平静。
他从地上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辨了辨方向,准备回自己平时藏身的破庙去。
走着走着,他的脑海中突然像电光火石一般,浮现出白天城门口的那幕打斗场景。
那个壮汉挥舞巨斧的凶猛,那个卖烧饼老汉出手的迅疾,一招一式,都清晰地在他脑海中重现。
“喝!” 想到兴头上,他突然一拳向前打出,嘴里还不由自主地发出一声大喝,紧接着,又学着那壮汉的样子,一掌斜劈而下。
“嘶 ——” 黑暗中,他的手掌结结实实地劈在了城墙上,一股痛彻心扉的感觉从手掌传来,疼得他眼泪都不由自主地吧嗒吧嗒往下掉。
“怎么不对呢?” 小叫花子揉着生疼的手掌,眼睛里汪着泪水,嘴里不解地嘀咕着,“明明那老者打出来的一掌虎虎生风的,我亲眼看到他一掌就将那个大汉的板斧拍开了啊,为什么我打出来就这么疼呢?”
“到底哪里错了呢?” 他一边嘀咕着,一边继续往前走着,脑海里还在不停地回想刚才的动作。
“嘭咚!”
一声闷响,伴随着小叫花子的痛呼:“哎呦,什么东西又绊了我!”
小叫花子只觉得脚下一绊,身体顿时失去平衡,“嘭咚” 一声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
他心里顿时充满了牢骚,今天真是倒霉,先是被石头撞了头,现在又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绊了一跤。
已经是亥时了,月光更加皎洁,城墙投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笼罩着小叫花子。
他趴在地上,有些气急败坏地四处摸索着,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又绊了他。
“咦,怎么会有一本书呢?” 他的小手在地面上摸索着,突然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方方正正的东西,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一本用线装订的书,封面是黑色的,已经有些破旧了。
他另一只手继续摸过去,却感觉摸到了一些黏糊糊的东西,像是某种液体。
“啊!鬼啊!”
小叫花子的手突然摸到了一个软软的、温热的东西,像是人的皮肤。
他顺着那东西往上摸,摸到了一个圆圆的、带着两个孔的东西——那是人的鼻子!
借着皎洁的月光,他定眼一看,赫然发现自己刚才绊倒的,竟然是一个人的腿!
整个人顿时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从地上猛地弹了起来,手里还紧紧抓着那本黑色的书,尖叫着拔腿就跑。
他跑出去老远,才敢回头看了一眼。
月光下,那个躺在地上的身影一动不动,正是白天被卖烧饼老汉一掌拍死的那个星宿庄壮汉。
而他刚才摸到的黏糊糊的东西,无疑就是早已凝固的血迹。
小叫花子吓得魂飞魄散,也顾不上辨别方向了,只是闭着眼睛,拼尽全力往前跑,仿佛身后有厉鬼在追赶一般。
他手中紧紧攥着那本从尸体旁摸到的黑色书籍,书页的边角割得他手心生疼,可他却丝毫没有察觉。
夜风吹过,卷起地上的尘土,也吹散了他的惊叫声。
滁州城下,只剩下那具冰冷的尸体,和散落一地的烧饼碎屑,在月光下无声地诉说着白日的喧嚣与血腥。
而那个惊慌失措的小叫花子,以及他手中那本神秘的黑色书籍,却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即将在这波澜壮阔的江湖中,激起一圈圈未知的涟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