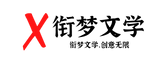1978 年的深秋,北方的风已经带着刀子似的凉意。
火车站广场上堆着半人高的垃圾堆,烂菜叶混着煤渣冻成硬壳,几只灰鸽子缩着脖子啄食,被突然响起的汽笛声惊得扑棱棱飞起。
哲野背着洗得发白的帆布包,站在出站口的台阶上。
裤脚还沾着农村的黄土,深蓝色卡其布中山装的肘部磨出了毛边,可他脊背挺得笔直,像株被风雪压过却没折腰的白杨树。
他刚在公社的办公室签完最后一笔字,结束了整整十年的插队生涯 —— 从 25 岁到 35 岁,人生里最该饱满的年月,全耗在了黄土地的日出而作里。
口袋里揣着邱非托人转来的信,说给他在设计院找了个临时绘图的活儿,先干着,等正式编制的名额。他捏了捏信纸边角,指腹触到粗糙的纸面,忽然想起离开北京那年,叶兰也是这样把一封情书塞给他,红着脸说 “等你回来”。
风卷着碎纸片打在他鞋上,他低头去捡,却听见极轻极细的一声 "咿呀"。
不是鸽子叫,也不是风声。
垃圾堆旁围着几个候车的旅人,指指点点。他拨开人群走过去,看见个被旧棉袄裹着的小婴孩,脸冻得通红,却睁着双乌溜溜的眼睛,睫毛上还挂着点白霜。她不像别的弃婴那样哭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躺着,看见他弯腰,忽然咧开没牙的嘴,露出个极灿烂的笑。
那笑容像突然炸开的小太阳,把周遭的灰败都照得透亮。哲野的心猛地一缩,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他想起父母被红卫兵带走那天,也是这样的深秋,母亲塞给他一块温热的糖,说 "阿野要好好的"。
"这娃子怕不是冻坏了。" 有人叹着气,"扔在这儿,等不到天亮就得......"
哲野没再听下去。他解开帆布包,把里面那件母亲留给他的羊毛毯掏出来,小心翼翼地裹住婴孩。小家伙在他怀里蹭了蹭,小脑袋往他胸口拱了拱,发出满足的哼唧声。
他抱着她往设计院的临时宿舍走。风刮得更紧了,他把孩子护在怀里,自己半边肩膀很快冻得发麻。路过街角的新华书店,玻璃窗里正摆着新到的《诗经》,封面上印着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小脸,那点笑意还残留在嘴角。
"就叫你陶夭吧。" 他轻声说,"陶是陶瓷的陶,经得起岁月烧;夭是夭夭的夭,活得亮堂。"
哲野的宿舍在设计院老家属楼的顶层,一室一厅,墙皮剥落,墙角结着蛛网。他花了整整两天收拾:扫掉积灰,用石灰水刷白墙壁,把捡来的旧书桌擦得锃亮,又在窗台上摆了盆从郊外挖来的野菊。
陶夭的小床是邱非送的,是他女儿用过的旧木床,栏杆上刻着歪歪扭扭的小鸭子。哲野给床板铺了三层棉絮,再罩上洗得发白的碎花床单,倒也软和。
最初的日子兵荒马乱。陶夭半夜总哭,不是饿了就是尿了。哲野白天在设计院描图,晚上抱着她在房间里打转,哼着跑调的《东方红》哄她睡。有次他实在太困,抱着孩子坐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时天已微亮,孩子正叼着他的手指吮得香,口水浸湿了他的袖口。
他去百货大楼买奶粉,柜台里的售货员打量他:"同志,给娃买的?"
"嗯。" 他应着,指尖划过玻璃罐上的价格标签,眉头微蹙。临时绘图员的工资不高,除去房租和口粮,剩下的刚够买最便宜的奶粉。
"这娃长得真好。" 售货员笑着递过奶粉,"眼睛跟画里的似的。"
他低头看了看怀里的陶夭,她正睁着眼睛看货架上的糖纸,小拳头攥得紧紧的。他忽然觉得,那些被黄土埋掉的十年,那些夜里惊醒的噩梦,好像都被这双眼睛照得淡了。
陶夭会爬的时候,最喜欢在书房打转。哲野画图时,她就坐在地板上,抓着他掉在地上的铅笔头啃。有次他正画着教学楼的结构图,忽然觉得裤腿被扯了扯,低头看见陶夭举着块橡皮擦,咿咿呀呀地对着图纸上的线条比划。
他失笑,把她抱到腿上:"这是承重墙,擦不得。"
她听不懂,只是用小脸蹭他的下巴,口水沾了他一脖子。他腾出一只手,在废图纸上画了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旁边写着 "陶夭"。她伸手去抓笔尖,他就握着她的小手,一笔一划地教她写 "夭" 字。
阳光透过老式木窗照进来,在图纸上投下格子状的光斑。灰尘在光柱里跳舞,陶夭的笑声像碎珠子,滚落在满室的墨香里。
陶夭上小学那天,哲野特意请了半天假。他给她梳了两条麻花辫,系上红绸子,又把邱非女儿穿过的蓝布校服熨得笔挺。
"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别跟同学打架。" 他蹲下来帮她系鞋带,手指有些抖。
"叔叔,你会来接我吗?" 陶夭拽着他的衣角,眼睛里有点怯。
"会。" 他摸摸她的头,"放了学,叔叔就在校门口的老槐树下等你。"
可第一周没过完,麻烦就来了。
那天哲野去接陶夭,看见她背着书包站在槐树后,肩膀一抽一抽的。他跑过去,发现她脸上有两道泪痕,辫子也散了。
"怎么了?" 他慌了,撩起她的袖子看,"有人欺负你?"
陶夭咬着嘴唇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抽噎着说:"他们...... 他们说我是野种,说我没有爸爸妈妈......"
哲野的心像被针扎了下。他把陶夭抱起来,看见不远处几个半大的男孩正对着他们做鬼脸。他深吸一口气,抱着陶夭走过去。
那几个男孩见他高大,往后缩了缩。带头的胖小子梗着脖子喊:"本来就是野种!我妈说的,没人要的娃才会被捡回来!"
哲野没动怒,只是把陶夭放下来,牵着她的手,平静地看着那几个孩子:"你们说她是野种?"
孩子们没人应声,却都带着挑衅的眼神。
"那你们看看。" 哲野扯了扯陶夭的校服,"这衣服是新熨的,每天换一套;她书包里的铅笔,是上海产的自动铅笔;早上她喝牛奶吃面包,你们吃的是什么?"
胖小子嘟囔:"我吃油条......"
"她晚上睡觉踢被子,有人起来给她盖;她发烧了,有人整夜抱着她不睡。" 哲野的声音不高,却带着股不容置疑的劲儿,"你们有谁能说,你们的爹妈能做到这些?"
孩子们愣住了。有个瘦小的男孩小声说:"我妈...... 我妈总骂我......"
"她不是野种。" 哲野把陶夭往身后护了护,眼神冷下来,"她是我哲野的女儿,比亲生的还宝贝。以后谁再敢胡说,别怪我不客气。"
他的目光扫过那几个孩子,他们吓得往后退了几步,扭头就跑。
陶夭从他身后探出头,小声说:"叔叔,你刚才好凶。"
他蹲下来,用袖子擦去她脸上的泪:"对坏人,就得凶点。"
那天晚上,哲野给陶夭煮了她最爱吃的鸡蛋羹,上面撒了点葱花。陶夭捧着小碗,忽然说:"叔叔,你就是我爸爸,对不对?"
哲野的手顿了顿,随即笑了:"傻丫头,我是你叔叔。"
"可邱叔叔说,爸爸就是会保护你的人。" 陶夭眨巴着眼睛,"你保护我了。"
他没再说话,只是往她碗里又添了半勺香油。窗外的月光落在陶夭的脸上,像层薄薄的银霜。他想,有些称呼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要让这孩子知道,她不是没人要的。
陶夭渐渐长大,书房成了她最常待的地方。
哲野的书桌靠着南窗,上面总摆着绘图板、三角尺和削得尖尖的铅笔。书架从地面顶到天花板,塞满了建筑类的书,也有几本童话和诗集 —— 那是特意给陶夭买的。
每天放学后,陶夭就坐在书桌旁的小凳子上写作业。哲野画图累了,会回头看她一眼,她要么咬着铅笔头皱眉,要么趴在本子上偷偷画画。有次他凑过去看,发现她在算术本背面画了个小人,穿着他常穿的中山装,旁边写着 "叔叔"。
"画得不像。" 他笑着弹她的额头,"叔叔有这么胖吗?"
陶夭红着脸把本子合上:"就是像!"
周末的午后,阳光最好。哲野会泡两杯茶,一杯浓茶自己喝,一杯加了冰糖的给陶夭。他看书,她就趴在地毯上翻画册。有次她翻到本讲故宫的书,指着太和殿的屋檐问:"叔叔,这个角为什么要翘起来?"
"那叫飞檐。" 他放下书,拿起铅笔在纸上画,"一来好看,二来能让雨水流得更快,三来...... 老辈人说,能让龙王爷顺着角飞上天。"
陶夭瞪大眼睛:"真的有龙王爷吗?"
"傻丫头。" 他敲敲她的脑袋,"是古人的念想,希望房子不漏水,日子安稳。"
她似懂非懂地点头,又指着画册上的雕花纹路问东问西。哲野耐心地答,从斗拱讲到榫卯,从青砖讲到琉璃瓦。阳光照在他脸上,鬓角的碎发泛着浅金,侧脸的线条在光里显得格外柔和。
陶夭忽然觉得,叔叔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比书里的飞檐还亮,比窗台上的野菊还暖。
有天晚上,陶夭起夜,看见书房还亮着灯。她扒着门缝往里看,哲野正趴在桌上画图,眉头紧锁,手里的铅笔在图纸上反复涂改。桌角的茶杯空了,烟灰缸里堆着烟蒂。
她悄悄倒了杯热水进去,放在他手边。他吓了一跳,回头看见她,眼里的疲惫淡了些:"怎么还没睡?"
"叔叔也早点睡。" 她指着图纸,"很难画吗?"
"有点复杂。" 他揉了揉太阳穴,"这是给山区学校画的教学楼,得结实,还得省钱。"
陶夭踮起脚,看见图纸上的房子矮矮的,窗户却很大。"为什么窗户这么大?"
"山里的孩子,得多见点光。" 他笑了笑,"你小时候也总爱往亮处凑。"
她想起自己小时候总爱趴在窗台上晒太阳,原来他都记得。她帮他把台灯往图纸边挪了挪:"叔叔,我帮你研墨吧?"
他失笑:"现在都用钢笔了,傻丫头。"
那天晚上,陶夭躺在床上,听着书房里传来的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觉得格外安心。就像小时候听着他的呼噜声,知道他就在隔壁,天塌下来都不怕。
陶夭八岁那年,设计院的李阿姨给哲野介绍了个对象。
女人姓周,是附近小学的语文老师,穿着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第一次来家里时,她拎着袋苹果,进门就笑着夸陶夭:"这孩子真俊,跟画上的似的。"
陶夭躲在哲野身后,不太喜欢她。她的笑太甜,甜得像供销社卖的水果糖,有点假。
周老师来得很勤,有时带本童话书给陶夭,有时帮着哲野收拾屋子。她总趁哲野不在时问陶夭:"你想不想要个妈妈?"
陶夭不说话,只是低头抠手指。
有次哲野去设计院加班,周老师留下来给陶夭辅导作业。她看着陶夭的练习册,忽然叹了口气:"你这字写得真好,可惜......"
"可惜什么?" 陶夭抬头看她。
"可惜没个亲爹妈教。" 周老师摸着她的头,语气轻飘飘的,"你说你亲爹妈怎么就把你扔了呢?是不是你不听话?"
陶夭的脸一下子白了。她想起学校里那些骂她野种的话,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有叔叔。" 她小声说,声音发颤。
"叔叔再好,也不是亲的呀。" 周老师笑了笑,"等我跟你叔叔结婚了,我当你妈妈,比你亲妈对你还好,好不好?"
陶夭猛地站起来,把练习册往桌上一摔:"我不要!我只要叔叔!"
周老师愣住了,脸色有点难看。就在这时,哲野推门进来,手里还提着给陶夭买的糖葫芦。他看见屋里的情形,眉头皱了皱。
"怎么了?" 他把糖葫芦递给陶夭。
周老师赶紧站起来,脸上又堆起笑:"没事,跟夭夭闹着玩呢。"
哲野没说话,只是看了看陶夭通红的眼睛,又看了看周老师。他沉默了几秒,忽然说:"周老师,谢谢你来辅导夭夭,时候不早了,我送你下去吧。"
语气客气,却带着不容拒绝的疏离。
那天晚上,陶夭躺在床上,听见哲野在客厅打电话。他的声音不高,但她听得清:"...... 算了,不合适。夭夭怕生,我不想委屈孩子...... 嗯,麻烦你了李姐。"
挂了电话,哲野走进来,坐在她床边。"还在生气?"
陶夭摇摇头,往他怀里钻了钻。"叔叔,你不要我了吗?"
"傻话。" 他拍着她的背,"叔叔什么时候都要你。"
"那你以后不要找别人好不好?" 她抱着他的脖子,声音闷闷的,"就我们俩,像以前一样。"
哲野沉默了很久,久到陶夭以为他睡着了。然后,他轻轻 "嗯" 了一声。
窗外的月光落进来,照在哲野的脸上。陶夭看见他眼角有亮晶晶的东西,像天上的星星。
陶夭上初中那年,个子蹿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哲野的肩膀。她开始穿碎花裙子,头发留长了,扎成马尾,走路时辫子在背后一晃一晃的。
哲野似乎也老了些。眼角有了细纹,鬓角冒出几根白发。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总穿中山装,陶夭用自己攒的零花钱给他买了件米白色的羊毛衫,他穿上,站在阳光下,倒比年轻时多了几分温润。
"叔叔,你这样像教书先生。" 陶夭歪着头看他。
"不好吗?" 他笑着转了个圈。
"好。" 她低下头,心脏忽然跳得有点快。
有次学校组织春游,要去郊外的植物园。前一天晚上,哲野帮她收拾背包,把面包、汽水、创可贴一样样往里塞。"山里凉,多带件外套。" 他把自己的蓝布外套叠好放进去,"别跟同学跑太远,有事就找老师。"
"知道啦。" 陶夭看着他忙碌的背影,忽然说,"叔叔,你也一起去好不好?"
他愣了愣,随即笑了:"叔叔要上班呢。"
那天在植物园,同学们都在看樱花,陶夭却总想起哲野。她看见有个男生的爸爸背着相机,一路给儿子拍照,忽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如果哲野也在,会不会也这样给她拍照?会不会把她举起来,让她够到最高的那朵樱花?
回来的路上,有个男生跟她表白,递了封情书。陶夭没接,只是摇摇头:"我不喜欢你。"
男生追问:"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她想起哲野看书时的样子,想起他帮她系鞋带时的样子,想起他把外套给她时的样子。她没说话,只是红了脸。
晚上回家,她把这事告诉了哲野。他正在画图,闻言抬起头:"哦?那你怎么想的?"
"我觉得他太幼稚了。" 陶夭说,"说话总爱吹牛,还总跟同学打架。"
哲野笑了:"我们夭夭眼光还挺高。"
"才不是。" 她小声说,"我就是觉得,他不如......"
不如你。
后面三个字没说出口,她怕他听了会生气。
哲野似乎没察觉她的异样,只是说:"谈恋爱不急,等你长大了,遇到真正好的人再说。"
她点点头,转身去厨房倒水。路过镜子时,看见自己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她摸了摸发烫的脸颊,忽然懂了 —— 原来有些喜欢,不是对叔叔的依赖,是别的什么。像春天的花,藏不住的,总会冒出来。
陶夭考上南方的大学那天,哲野请了邱非来家里吃饭。邱非看着录取通知书,拍着哲野的肩膀:"行啊老哲,养了个大学生出来!"
哲野笑着给邱非倒酒,眼睛却一直看着陶夭,像是怕她飞了似的。
去学校报到那天,哲野送她去火车站。他帮她拎着大箱子,里面塞满了换季的衣服、常用的药,还有几本她喜欢的诗集。
"到了学校记得给家里打电话。" 他把车票递给她,"食堂的饭要是吃不惯,就自己买点东西补补。"
"知道了。" 陶夭看着他鬓角的白发,忽然舍不得走了。
"缺钱就跟我说,别委屈自己。" 他又从口袋里掏出个信封,塞到她手里,"这是给你买零食的。"
陶夭捏着信封,厚厚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叔叔,你也照顾好自己,少抽烟,早点睡。"
火车开动时,她从窗户里往外看,看见哲野站在月台上,挥着手,身影越来越小。她捂住嘴,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大学的日子新鲜又忙碌。陶夭学的是中文,每天泡在图书馆里,看诗经,读宋词,日子过得安静。有男生追她,有的送花,有的约她看电影,她都婉拒了。
他们总说些 "我喜欢你"、"我会对你好" 的话,可陶夭总觉得,这些话太轻了,像风一吹就散的蒲公英。她见过真正的好,是十年如一日的照顾,是藏在细节里的惦记,是哲野那样,不说爱,却把爱融进了柴米油盐里。
周末她总往家里打电话,听哲野说单位的事,说邱非又来蹭饭了,说窗台上的野菊开了。有时她会问:"叔叔,你一个人吃饭吗?"
"嗯,随便下点面条就行。" 他说得轻描淡写。
可她知道,他肯定又对付着吃了。以前她在家时,他总变着花样给她做吃的,自己却常啃馒头就咸菜。
二十岁生日那天,她接到哲野的电话,说给她寄了个包裹。拆开一看,是枚红宝石戒指,衬着丝绒盒子,红得像跳动的火苗。还有张纸条,上面写着:"夭夭长大了,该有件像样的首饰了。"
同宿舍的女生围着戒指啧啧称奇:"这得多少钱啊?你爸对你真好!"
陶夭摸着戒指,忽然想起小时候他给她买奶粉的样子。她把戒指戴在无名指上,大小刚刚好,像是量着她的手指买的。
寒假回家,她戴着戒指给哲野看。他笑了:"挺好看,我们夭夭戴什么都好看。"
"太贵了。" 她小声说。
"不贵。" 他摆摆手,"只要你喜欢就行。"
那天晚上,她帮他整理衣柜,看见他那件米白色的羊毛衫放在最上面,洗得有些发白了,却依旧平整。她想起自己挑这件衣服时说的话:"叔叔穿这件显年轻。"
原来有些话,他都记得。她抱着羊毛衫,忽然想,就这样吧,一辈子陪着他,不谈恋爱,不嫁人,也挺好。
陶夭大三那年的春天,接到哲野的电话,说邱非要来学校看她。
她挺高兴,买了水果放在宿舍等着。可等来的不只是邱非,还有个陌生的女人。
"夭夭,这是叶阿姨。" 邱非笑着介绍,"是你叔叔的老朋友。"
叶兰穿着米色风衣,头发烫成波浪卷,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早就听你叔叔提起你,果然是个漂亮姑娘。"
陶夭礼貌地笑了笑,心里却有点发紧。她听过这个名字,八岁那年,邱非在电话里提到过。
叶兰很会说话,问她学校的事,问她的专业,还说哲野总跟她讲陶夭小时候的趣事。"他说你三岁时偷喝他的酒,醉得抱着桌子腿喊叔叔。"
陶夭的脸有点红,心里却像被什么堵住了。她看着叶兰看她的眼神,那种亲昵,像是已经把她当成了家人。
送走他们后,陶夭坐在宿舍里,心里乱糟糟的。她想起哲野电话里的语气,比平时轻快些,像是有什么喜事。她不敢想,却又忍不住想 —— 叶兰是他年轻时的恋人,现在她丈夫去世了,他们是不是要在一起了?
周末回家,她故意问哲野:"叔叔,邱叔叔说你最近挺忙?"
"嗯,跟你叶阿姨......" 哲野顿了顿,"联系上了,偶尔见见面。"
陶夭的手猛地一颤,手里的茶杯差点掉下来。"哦。"
"她人挺好的。" 哲野看着她,眼神里带着点试探,"你觉得......"
"挺好的。" 陶夭打断他,低下头,假装喝茶,"你们要是...... 要是想在一起,我没意见。"
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可她不敢抬头看哲野的眼睛。
那天晚上,她一夜没睡。想起小时候他护着她骂那些男孩,想起他拒绝周老师时说的 "我不想委屈孩子",想起他给她买的红宝石戒指。原来这些,都可能只是叔叔对侄女的好。原来他心里,始终有个叶兰。
她病了,发着高烧,躺在床上,总梦见哲野穿着西装,牵着叶兰的手,对她说:"夭夭,叫妈妈。"
她从梦里惊醒,浑身是汗。同宿舍的女生吓坏了,要送她去医院,她摇摇头,只是想回家。
哲野接到学校的电话时,正在画一张图书馆的结构图。电话里说陶夭高烧不退,已经送到医院了,他手里的铅笔 "啪" 地掉在地上。
他请了假,坐最早一班火车赶过去。到医院时,陶夭正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嘴唇干裂,还在昏睡。
"医生说她是病毒性感冒转肺炎,烧到 39 度多。" 同宿舍的女生说,"她总说想家,还说胡话,喊你的名字。"
哲野的心像被刀剜了下。他坐在床边,握住陶夭滚烫的手,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他的。
"夭夭,叔叔来了。" 他轻声说,声音发哑。
陶夭似乎听见了,眉头动了动,嘴里嘟囔着:"别...... 别结婚......"
哲野愣住了。他看着她烧得通红的脸,忽然明白了什么。那些他刻意忽略的细节,那些她躲闪的眼神,那些她对叶兰的疏离 —— 原来不是他想多了。
他给叶兰打了个电话,声音很平静:"叶兰,对不起,我们可能不合适。"
"为什么?" 叶兰的声音带着惊讶,"是因为陶夭吗?"
"她还小,离不开我。" 他没说更多,只是道了歉,挂了电话。
陶夭醒过来时,看见哲野趴在床边睡着了,眼下有浓重的青黑。他的头发乱了,衬衫的袖子卷着,露出小臂上的青筋。
她伸出手,想摸摸他的头发,可手刚抬起来,就被他抓住了。
"醒了?" 他猛地睁开眼,眼里满是惊喜,"渴不渴?想不想喝水?"
她摇摇头,眼泪掉了下来。"叔叔,你没走?"
"傻丫头,我走了谁照顾你。" 他给她擦眼泪,"饿不饿?我给你买了粥。"
住院的那几天,哲野一直陪着她。他给她削苹果,读她带来的诗集,晚上就趴在床边睡。有次她半夜醒来,看见他正往她手里塞暖水袋,动作轻得像怕吵醒她。
"叔叔,你回去吧,我没事了。" 她小声说。
"等你好了再说。" 他掖了掖她的被角,"医生说你还得养几天。"
她看着他布满红血丝的眼睛,忽然说:"叔叔,对不起。"
"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他笑了笑。
"我不该生病的,耽误你......" 耽误你和叶兰。
后面的话没说出口,他却懂了。他摸了摸她的头,语气很轻:"跟她没关系。是我想明白了,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人是你。"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神温柔得像水。陶夭的心脏猛地一跳,她知道,有些话,他没说,可她懂了。
陶夭毕业那年,哲野被查出肝癌晚期。
医生把她叫到办公室,说最多还有一年时间。陶夭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梧桐叶落下来,忽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她没哭,只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冷。
她没告诉哲野实情,只是说他得了肝炎,需要好好休养。她辞掉了城里的工作,回了家,每天陪着他。
哲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却没问。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看书,画图,只是动作慢了些,脸色也越来越差。
每天吃过晚饭,他们会去楼下散步。陶夭挽着他的胳膊,他的手臂瘦了很多,硌得她手心发疼。
"夭夭,找个男朋友吧。" 他忽然说,"我看邱非的侄子就不错,人老实,工作也稳定。"
陶夭摇摇头:"不找。"
"傻丫头,我不能陪你一辈子。" 他叹了口气,"总得有人照顾你。"
"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她把他的胳膊挽得更紧了,"你也会好起来的,我们还要一起住很多年。"
他笑了笑,没再说话。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两条交缠的线。
哲野的身体越来越差,后来连下床都困难了。陶夭请了个钟点工中午来做饭,其余时间都自己守着。她给他擦身,喂饭,读他喜欢的建筑杂志。
有次她给他读一篇讲苏州园林的文章,他忽然说:"以前总想着,等你嫁人了,就带你去苏州看看,那里的亭子飞檐最好看。"
陶夭的眼泪掉在书页上,晕开了墨迹。"我们以后去,等你好了就去。"
他笑了笑,闭上眼睛,像是累了。
那天晚上,陶夭在书房整理东西,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她想起哲野说过,有一叠东西不准她动。她找了把小钥匙,打开了盒子。
里面是几本日记。
她翻开第一本,字迹还很年轻:"1978 年 11 月,捡到个小丫头,笑起来像太阳。给她取名陶夭,希望她活得亮堂。"
第二本:"1985 年 6 月,夭夭被人骂野种,我揍了那几个小子。她抱着我哭,说怕我不要她。傻丫头,我怎么会不要你。"
第三本:"1995 年 3 月,叶兰回来了。可我看见她,心里想的却是夭夭在学校吃没吃好。我知道,我这辈子,栽在这丫头手里了。"
第四本:"2000 年 5 月,医生说我时间不多了。夭夭这孩子,看着坚强,其实心软。我走了,她怎么办?得找个人替我疼她。"
陶夭抱着日记本,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纸页上。原来他什么都知道,知道她的心思,知道自己的病情,知道她害怕什么。他什么都不说,只是默默地,用尽全力护着她。
过了几天,日记本不见了。陶夭知道,是哲野藏起来了。他不想让她知道他知道,就像他一直以来,把所有的爱都藏在心里。
2001 年的春天,哲野走了。
那天早上,阳光很好,窗台上的野菊开了几朵。他握着陶夭的手,气息很弱:"夭夭,要好好的...... 找个好人家......"
陶夭点点头,眼泪掉在他手背上。"我知道。"
他笑了笑,眼睛慢慢闭上了。
葬礼那天,邱非拍着她的肩膀:"你叔叔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
陶夭没哭,只是给哲野鞠了三个躬。她知道,哭没用,他希望她好好的。
回到家,她在书桌抽屉里发现一封信,是哲野的字迹:"夭夭,我去了。可以想我,但别总想着我。你过得好,我才安心。叔叔。"
她把信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晚上整理书房,她在柜子角落里发现个满是灰尘的陶罐。洗干净了,才看见上面刻着字,是颜体,笔力遒劲:
" 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
陶夭抱着陶罐,忽然蹲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原来他什么都懂。懂她没说出口的爱,懂她藏在眼底的依恋,懂她看着他鬓角白发时的心疼。
他比她大三十岁,她出生时,他已历经沧桑;她长大时,他已步入暮年。他们错过了最好的时光,却用一辈子的陪伴,把遗憾酿成了温暖。
窗外的月光落进来,照在书房的书桌上。那里还放着哲野没画完的图纸,铅笔尖上,仿佛还留着他的温度。
陶夭擦干眼泪,把陶罐放在窗台上,挨着那盆野菊。她想,她会好好的,像他希望的那样,活得亮堂,活得安稳。
因为她知道,他从未离开。他在春风里,在月光里,在她读过的每一首诗里,在她走过的每一段路上。
就像他说的,只要她过得好,他就安心。
而她的好,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